買了柏林第三的咖啡豆Fjord來試試,包裝很精美。在路上童裝店看到Jellycat玩偶,跟它們很不熟,為什麼最近這麼紅?而且cat在哪?週六午後朋友陪我去選參加婚禮的西裝,平常超少穿正裝,果然正裝不管誰穿都顯得人模人樣。後來才發現服務我的小哥是雙胞胎,而且兄弟倆都在同間店工作,一開始讓人好迷惑XDD。突然回暖好熱。去吃了日本蛋糕,抹茶就是爽。朋友聊到她最近聽podcast才知道呱吉以前年輕時交的都是男友,還說後來跟女生交往是因為跟男生交往太花錢,我整個WHAT?!
2025年全球生活工作平衡指數,日本、台灣跟南韓剛好排名29、30、31。評判標準包含年假、產假、最低工資、病假薪資、健保、幸福指數、平均工時、安全和平指數跟LGBTQ+包容性等等。前五名分別是紐西蘭、愛爾蘭、比利時、德國跟挪威。亞洲第一是新加坡第25名,馬來西亞第27名。





《摩訶婆羅多》裡說國王必須向人民徵稅1/6,在古代算重稅了。春秋前的井田制稅1/9已經不低,因為還要加上徭役等勞動。秦漢之後還有人頭稅、鹽鐵稅。春秋魯國曾推行過「初稅畝」也是跟歐洲教會收的什一稅相當。不過印度古代的公共建設主要是由首陀羅負責,而繳稅群體是吠捨跟首陀羅。所以說1/6的稅再加上勞動付出(恐怕只多不少),平民老百姓的生活應該不是很容易。德國一般中產林林總總的稅加起來大概是十稅三四,台灣稅十稅一二。
最近發現居然有百日郵輪這種東西,還沒坐過超過三天的大郵輪,百日郵輪好心動,但要價一個人至少五十萬台幣。查了一下居然是Cunard Line。提到Cunard Line就想到1915年RMS Lusitania(盧西塔尼亞號)的重大船難,大家比較熟悉三年前的鐵達尼沉沒,盧西塔尼亞比較不知名。最近剛好看了一部關於盧西塔尼亞沉沒的紀錄片。一戰時期盧西塔尼亞在愛爾蘭外海被德國潛水艇魚雷擊中(兩次)而沉沒。她當時約載將近兩千人,其中約一千兩百人喪生(約有一百個孩童,鐵達尼則是一千五百人喪生)。跟鐵達尼很不同的是盧西塔尼亞整個沉沒只花了十八分鐘,鐵達尼支撐了兩小時四十分(所以音樂還能繼續)。
之前鐵達尼上救生船不夠,但盧西塔尼亞上的救生船其實是夠的,只是被魚雷擊中後船身劇烈傾斜,要降下救生船變得很困難意外頻出。當時海水溫度約十一度,即使逃過被船身吸入水下的人也因為失溫而喪生。加上因為戰爭時期,即便離愛爾蘭海岸線二十公里,救援船隻也在沉沒後的一小時左右才抵達。鐵達尼之所以能被拍成愛情電影,大概因為它沉得慢。盧西塔尼亞18分怎麼拍都是恐怖片。是啊,情情愛愛最終還是跟長度有關。愛情需要起承轉合,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封鎖的場景只是自我哄騙的荒謬劇。但還是想搭百日郵輪(蛤)。
泳池三週整修完畢終於可以游了,但好像游得太急最後有點腳軟。附近的巷子封路準備重鋪柏油的樣子,還沒開始動工結果一堆人在裡頭塗鴉畫畫,非常柏林。小時候很納悶為何七夕是在鬼月,後來才知道七夕的歷史要早早早於鬼月。可能是古人看到別人一直放閃受不了就把鬼月訂在七月。





看完了《南方》,這本可以排進今年最愛小說前三名,非常喜歡。像是Marguerite Duras遇見張愛玲然後被王家衛拍成電影那般,南方濕熱的粵裔堂兄弟禁斷愛戀可以寫得如此雲淡風輕。點到為止卻又寫進心坎,實寫家庭虛描離散,拜託拍成電影。小說主角看著自己母親時這樣想著:「我那時才明白,我一生都在凝視她;我在她的世界裡,僅僅站在門檻邊,略帶疏離地望著她,不近不遠,卻又以某種無法言喻的方式,與她糾纏不清。」
他不喜濃烈的氣味,每早搭校車時,總被那些刮鬍水與香水的味道薰得反胃——如今卻讓他心動。多年後,每當他在某人皮膚上,或更衣室的空氣中,嗅到這種化學麝香的古龍水味,那種當下湧起的悸動便會再現,對他而言,這氣味象徵著可能,是一場午後、夜晚,甚或一生的徐徐展開。
開讀新書《誤導年代》,媒體識讀的失敗原因可能是忽略社群的影響力。關注焦點不能只是個人如何獲取訊息,而是在群體如何消化資訊。
自1990年代初以來,我們的社會結構已顯著轉向,從以社區為基礎、面對面的互動,轉變為線上互動。像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線上社群媒體,大幅增加了我們接收的社交資訊量及其速度,使社群效應相較於其他知識來源更具優勢。社群媒體也讓我們能夠建構和修剪我們的社交網絡,圍繞著與我們觀點和偏見相同的人,並拒絕與不同意見者互動。這反過來又過濾了世界回饋我們的方式,限制了我們接觸的事實。
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一種觀點,認為人類本質上是理性的,能夠巧妙地區分事實與虛構,並最終得出關於世界的永恆真理。這種思維方式認為人類遵循邏輯規則,準確計算機率,並根據所有可用資訊做出關於世界的決策。相反,無法做出有效且資訊充分的決策通常被歸咎於人類推理能力的不足──例如,源於心理抽動或認知偏差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我們的成功或失敗最終取決於個體是否理性和智慧。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得到更好的結果──更真實的信念、更明智的決策──我們就需要專注於提升個體的推理能力。社會學習模型幫助我們體認到,人類學習和理性的這幅圖景被嚴重扭曲了。我們從這些模型中看到,即使是完全理性的──儘管很簡單──個體在向社交網絡中的其他人學習時,即使擁有足夠多的證據,也可能無法形成關於世界的真實信念。換句話說,理性的個體可能會組成完全不理性的群體。
開讀新書《焦慮世代》,大概就是現在三十歲以下的人。「本書中的核心觀點是,現實世界的過度保護和虛擬世界的保護不足這兩種趨勢是 1995 年後出生的孩子成為焦慮世代的主要原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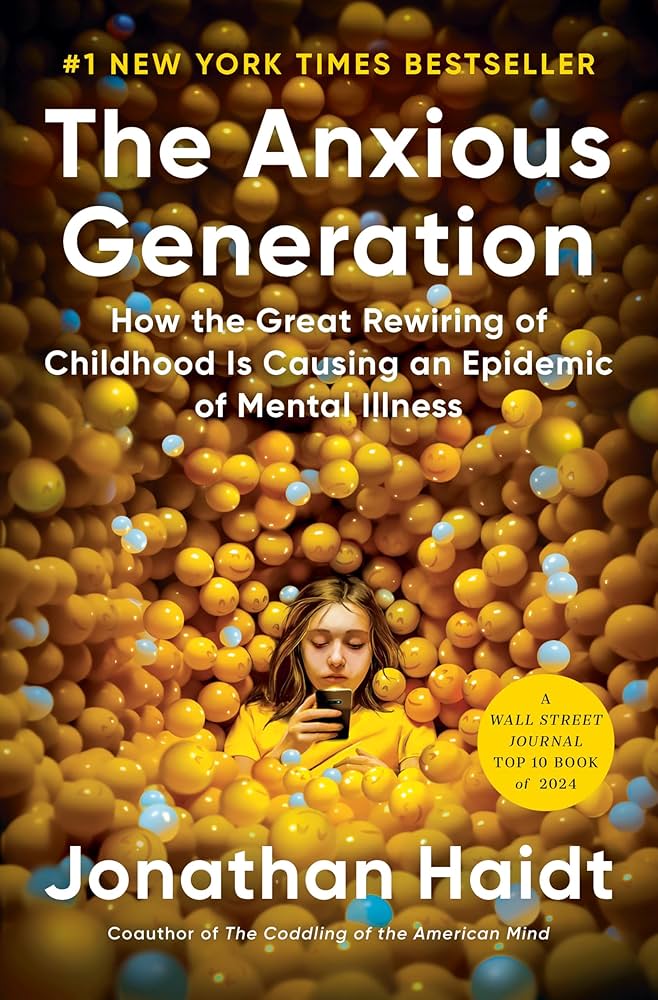
那些竭力透過心理技巧讓年輕人點擊從而最大化參與度的公司,才是罪魁禍首。這些公司在兒童脆弱的成長階段讓他們上鉤,他們的大腦正快速重塑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刺激。這其中包括對女孩造成最大傷害的社交媒體,以及對男孩最有吸引力的電子遊戲和色情網站⋯⋯雖然大腦中尋求獎勵的區域發育得更早,但大腦額葉皮質——負責自我控制、延遲滿足和抵制誘惑的關鍵部分——要到25歲左右才能完全發育,而青春期前的兒童正處於發育的特別脆弱的階段。當他們進入青春期時,他們往往缺乏社交安全感,容易受到同儕壓力的影響,也容易被任何看似能帶來社會認同的活動所誘惑。我們不會允許青春期前的兒童購買菸草或酒精,也不會讓他們進入賭場。與成年人相比,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的成本尤其高,而收益卻微乎其微。
《焦慮世代》書中作者也提到:
虛擬世界的聯繫通常發生在門檻較低的社群中,因此人們可以屏蔽他人,或在不滿意時直接退出。社群往往壽命短,關係也往往是一次性的。當人們在一個無法輕易逃離的社群中長大時,他們會做我們的祖先數百萬年來所做的事情:學會如何處理人際關係,如何管理自己和自己的情緒,以維持這些珍貴的關係。
這就是為何網路上常常有莫名其妙的論戰,加入任何社群成本太低、隨意發表言論成本太低、攻擊別人成本太低。但它的隱藏的成本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焦慮值爆發,信任破滅與社群瓦解。《摩訶婆羅多》也說了:
不要期望用爭吵的方式制服惡人。沒耐心,不忍讓,那是幼稚的行為。想要殺死敵人,就不應袒露一切。要克制自己的憤怒和不滿,即使不信任敵人,也要擺出信任的樣子。要說好聽的話,不要為難對方,不要毫無用處地表示仇恨,不要勞累嗓子。」不要勞累嗓子很重要唉XDD,面對敵人的策略是「一旦敵人的財富耗盡,也就容易控制。無論執著正法或非法,力量和財富是根本。它令敵人高興,應該剷除。當著敵人的面,貶斥人為努力,鼓吹命運。毫無疑問,聽天由命者迅速遭到毀滅。
《摩訶婆羅多》裡也提到一則老鼠與三貓的寓言。一天晚上,貓不小心落入獵人設下的陷阱,被網纏住無法動彈。老鼠發現貓被困後,本想趁機享用獵人留下的肉塊,但突然察覺到貓鼬從地面逼近(如果老鼠下地,就會被貓鼬吃掉),而貓頭鷹則在樹上虎視眈眈(如果老鼠留在陷阱上,就會被貓頭鷹抓走)。老鼠陷入絕境,意識到貓雖是敵人,但此刻是唯一能提供庇護的選擇。於是,老鼠主動向貓求和,說:「我們暫時結盟吧!你保護我免於貓鼬和貓頭鷹的攻擊,我來咬斷網繩救你脫困。」貓同意了,老鼠躲進貓的毛中避難,貓鼬和貓頭鷹見無機可乘,只好失望離去。脫險後,老鼠開始慢慢咬斷網繩,但不急於完成。貓變得焦急,催促老鼠快點。老鼠智慧地回應:「我不能現在就放你,因為你一自由就會吃掉我。我會等到獵人回來的那一刻再放你,那時你專注逃命,不會再想吃我,我也能順勢逃走。」果然,當獵人出現時,老鼠迅速咬斷最後的網繩,貓驚慌逃竄,老鼠也趁亂溜走,兩者都保住了性命。
書中悲觀認為:
他變得可愛有原因,他變得可憎也有原因。這個生命世界惟利是圖,沒有誰對誰可愛。同胞兄弟之間的情誼,夫妻之間的恩愛,在這世上,我不知道有無緣無故的愛⋯⋯精勤努力小心謹慎,預先保持對恐怖的警惕。應該心懷恐懼,有所準備有所警惕。從恐懼和謹慎中產生智慧。事先懼怕恐怖的人,到時候就不會懼怕,不知懼怕的人放鬆警惕,到時候會極度懼怕。決不要鼓勵別人『別害怕』。一個人知道自己無知,就會去請教有見識的人。因此懼怕而貌似不懼怕,不信任而貌似信任。
Be First to Comment